无谓错失清明谷雨,《取火》立夏把握暖光。
人生不能没有歌曲,借你耳朵听我歌唱。
五位写手一人一区,诚心推介音乐珍藏。
NOW ON >>> 中国户外音乐节品牌草莓音乐节
2019年的夏天,一档音乐综艺节目——《乐队的夏天》在爱奇艺播出了。这档围绕着中国独立乐队的综艺,那年夏天在首播后,掀起了一波关于中国独立音乐的热潮。再之后的几年中,爱奇艺乘势接着推出了第二季、第三季,使独立音乐在主流媒体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曝光。2022年,爱奇艺又播出了《我们民谣2022》,一档围绕着民谣风格的音乐竞演节目。节目汇集了来自不同年代的民谣音乐人,理念是“唱生活的歌”。这两档近期的音乐综艺让原本小众乐队和民谣歌手的粉丝飙升、巡演邀约不断。于是,越多年轻人走进Live House,冲进音乐节。

其实,摇滚和民谣对年轻人的吸引,并非近年兴起,而是一种历经沉淀后的厚积薄发。80年代末,中国开始与西方流行文化接轨,其中包括摇滚音乐。9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飞跃式的城市化,快速发展带来了个体的边缘化,许多年轻人感到自身被现实吞没。而摇滚,作为一种反叛、个人表达的载体,恰好回应了这种精神困境。
在中国,民谣与摇滚不完全是独立于对方的存在,而是纠缠着出现。例如同时参加了《乐队的夏天》和《我们民谣2022》的乐队——水木年华。他们的作品既可以是撕裂愤怒的呐喊,也可以是低吟浅唱的呢喃。不过,与摇滚不同的是,民谣是随着网络和音乐平台(例如虾米音乐、网易云音乐)的兴起,在2010年后才出圈。那年,宋冬野的《董小姐》刷爆了社交平台,赵雷的《成都》红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。民谣凭借着质朴的旋律,内心独白般的歌词,击中了漂泊无定的城市青年。
赵雷《成都》。(取自YouTube)
我也是从了解民谣开始了解独立音乐。印象中最早的记忆,是中学时期看的《中国好声音》,有一位选手翻唱了《逝去的歌》。那种略带苍凉却极具穿透力的歌声,和带着故事感的歌词被当时的我铭记。从那以后,我开始寻找类似风格的作品,也慢慢知道了“民谣”。

民谣一般唱童年、漂泊和梦境,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,绕开喧嚣的广场,在暮色中低声吟唱。听民谣的人,除了旋律,也会被背后的故事所打动,为一句歌词,而共鸣共情。而摇滚,则像暴风雨前骤然响起的雷,是旷野中执拗燃烧的篝火。鼓点轰鸣,吉他与贝斯交织成声浪。听摇滚的人,也许同样困顿、迷惘,却始终怀抱挣脱现实、放声呐喊的渴望。无论是哪一种风格,创作者们都在用音乐对抗庸常,寻找真实。
后海大鲨鱼在北京草莓音乐节表演《时间之间》。(取自YouTube)
去年五月,我趁着去北京交换的机会,参加了人生中第一场音乐节——草莓音乐节。无可否认,这个由中国最大的独立唱片公司摩登天空发起的户外盛会,在那晚点燃了春末的夜空。舞台上,我如愿听到喜爱的后海大鲨鱼、朴树与痛仰乐队。当后海大鲨鱼的前奏响起,正是北京郊区太阳落山的时候。夕阳斜照,洒在人海之顶,金色光泽在大家的发梢上跳跃。巨大的屏幕上,一只赤红野马在奔腾,自由肆意的泡泡在灯影微风中轻舞。此刻歌词响起,“我们像只野马一样在这城市里流淌,浪费了太阳也从不会感到悲伤。”
朴树的歌是随着夜幕一起降临的。他穿着墨绿色的工装外套,破洞牛仔裤,戴着墨镜和棕色头巾,还是流浪诗人的形象。歌声一落,便将那些似曾相识的悸动、离别的怅然、年少的理想与幻梦,轻轻召回。我想起音乐制作人张亚东在《我们民谣2022》中说的那句话。
民谣就是永远能够察觉到
张亚东
那种非常脆弱的、美好的东西
并且又能把它准确地表达出来
为何民谣让我们感动,因为他的歌像是生命结束时,悠悠的一声梵唱。

那次的音乐节让我离独立音乐更近了一步。我想与无论是摇滚还是民谣,独立音乐,归根结底,是在喧嚣浮躁的世界,拥有选择和坚守内心声音的自由。
同场加映 +++ 王璐琼《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》
PREVIOUSLY ON >>> 新加坡华语独立乐团Goose我鸟
王璐琼|《亲爱的任意门》专栏作者
欢迎推开这扇任意门,让漂浮着的符号找到归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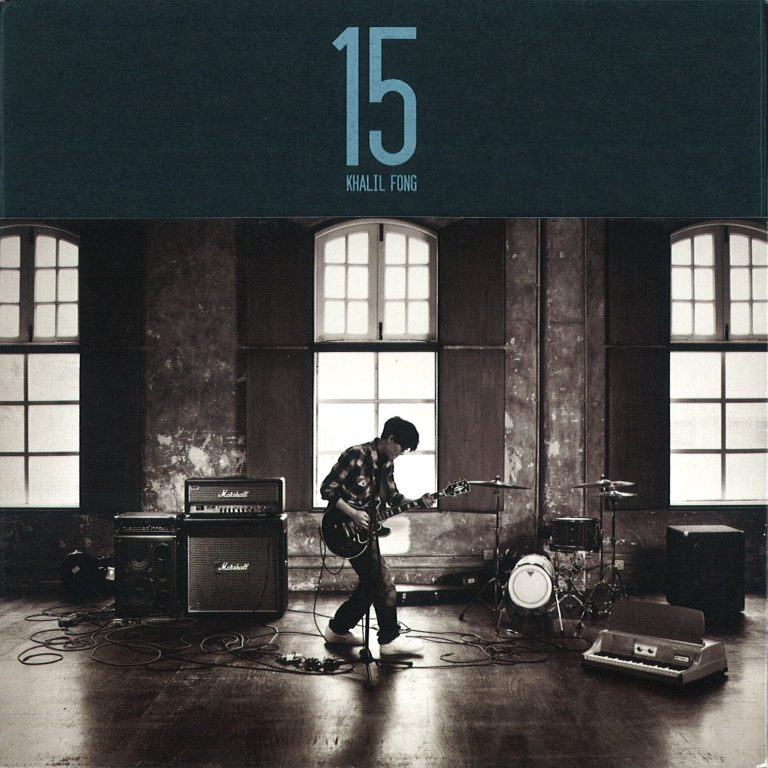
-768x1152.jpg)
